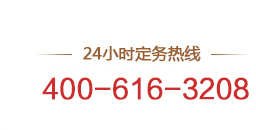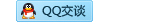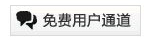新聞中心
當前位置:首頁 >> 新聞中心 >> 受文藝青年追捧的無印良品要大規模降價了受文藝青年追捧的無印良品要大規模降價了
雖然早前網上就有音信傳出稱今年8月1日開始MUJI(無印良品)將全線降價,不過此前商店里只有那些夏季打折的銷售廣告。假設你在這個8月初興趣旺盛跑去商店里問店員,得到的回答是“對不起,我們沒有接到調價通知。”
“之前那些降價的傳言部分有誤。”無印良品(上海)商業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山本直幸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該品牌最終的降價時間是8月21日。
這亦是MUJI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后最大格局的一次降價。
并非首次降價
吳艷婷是MUJI的忠誠粉絲。早在2005年MUJI第一家專賣店進入的時候,她就開始購買這家的物品,現在她依舊會“沒事就去公司對面的店里晃一圈。”
“逛著逛著就會發覺有很多小驚喜。”她說,先前沒有想著要買的小雜貨,看到介紹和設計覺得精巧且實用,于是就會放進購物籃竹席里,“決定回家試試看好不好用咯。”
因為同是日本國品牌的聯系,MUJI常被外界用來與優衣庫做對照,但山本直幸卻并認為兩者相同,他認為反而和另一家瑞典公司宜家比較更加合適一些,“因為在MUJI所出售的物品里,差不多有一半是生存雜貨類用品。”
實際上也確實如此。MUJI的商業狀態清楚更加“復雜”一些。這家以生存方法為擴大方位的公司在內部把自己的在銷物品分為三大塊兒:衣著、生存雜貨(電竹席產品、家居用品、文具)以及食品類,離別占比約為50%、48%、2%。在食品類貨品沒有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時,前兩者則是各占一半,“所以,你很難說MUJI畢竟是一家賣衣服的公司還是賣生存用品的公司。”
有“死忠粉”的追捧,但價格一直是MUJI被“指責”的一點。
這個日本國品牌誕生于1973年原油危機時,那個時期日本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國家經濟增加明顯放緩。MUJI最初的定位就是去品牌化,追求沒有logo,生產簡易包裝甚至不包裝的生存物品,以提供較低廉的價格給大眾消費者。
脫胎于西友連環的“超級市場貨”,如今卻是國內各家大型購物中心開業時的熱捧的招商對象。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價格也自然是水長船高。
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賣出的物品標價上平常會有日本國的定價。經過匯價折算,消費者便可能知道同一貨品在國外的售價。“平常國內的價格要比日本國的貴一倍。”吳艷婷說,正是因為如此,在去年日元匯價大跌時,她“乘機”去日本國掃了不少貨,“那里的MUJI可低廉了呢。”
也許是感到到了這一點。MUJI從2014年開始調整其物品定價。
換而言之,此次的降價并不是MUJI在華的首次降價。山本直幸向記者泄露,從去年至今,該品牌已經調過三次價。第一次是在2014年的秋季,主要是一些衣著和生存類用品降價;第二次則是在今年的春季,只對部分衣著進行了調價,而第三次則是將要到來的這次。
雖然并不是早前傳言的全線降價,但加上之前兩次,被調價的產品數量的覆或然率并不低。
無印良品上海總部促販部的王黎雋說給記者,一個品類有能夠有四五個SKU(即保存庫存掌握的最小可用機構)甚至更加多,目前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SKU一共有5000個支配,如此算來,三次調價后,取得“新定價”的物品占比并不小。
據政府給出的數據,2014年秋冬的首次降價占全體物品的12%支配,2015年春夏的服裝雜貨類占到當時春夏全服裝類物品的37%支配,最新的這一次降價則占到全體物品的近50%。
調價背后的理論
對于記者提出為什么要調價的事故,山本直幸如是回答,“我們盼望店里的物品價格定價合適,足以讓喜歡的它顧客在出手(購買)時毫不猶豫。”他以MUJI的護膚品為例,我們的打扮品根本上都是日本國進口的,通過特惠規范,關稅減輕規程的申請,我們盡能夠的將因為進口部分的費用降低,從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價調整到顧客更易接受的水平。
在上海正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CEO崔洪波看來,MUJI的此次降價有兩方面要素。“首先,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銷量增加讓它具有降價的能夠。”據知道,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沒有自己的制成廠,產品均為OEM代工,“隨著該品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迅速開拓,生產要求也隨著賣出量加大,生產成本就可能降下來了。”
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時的生產成本降低這一點也得到了山本直幸的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市場要求越來越大,一次的訂購量增多,訂購生產成本單位價格自然就降下來了。”
記者知道到,在MUJI尚未完全擴張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門店不僅數量少,賣出額也很低,根源無法達到代工廠的最低訂貨量。同時,由于出關物品均被附上日語吊牌,第二次進關后的售賣產品還大概需要另加中文吊牌,僅此一項,生產成本不菲。
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門店和賣出額的增加,這一規模開始擴大變化。2010年起,MUJI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大格局“內販”,到2012年,服裝已全部實現“內販”,生存雜貨用品的“內販”率亦達30%。如此一來,物流和吊牌生產成本成倍下降。
此外,MUJI還通過減少不良率的方法降低代工生產成本。此前,由于品牌方對于產品要求較高,所以代工廠次品率居高不下。對此這些代工廠往往會事前要求增加超過10%的代工費用。對準這一難題,MUJI派駐一名日籍本質擔負,親自動手制作樣品,追溯整個生產工藝流程,并最終處理難題。經此,代工廠次品率、材料與人工生產成本均大幅降低。
崔洪波指出,近年來MUJI在華市場的迅速拓張也推動了這家公司選擇降價方式的另一個原由,“降低價格以轉移更多的消費者。”
記者得到,雖然MUJI在2005年就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其在國內市場真正開始“發力”則是在2010年后。2010年開始,這家公司開始以一年兩位數的開店數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大。2013年,MUJI“發作式”的開了37家店,算是得到了社長金井政明之前設定的“百店”打算。據山本直幸泄露,去年新增了30家,“今年的打算應該和去年差不多。”
從開店數量來看,除了日本國本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已經是MUJI全球的第二大市場(這一點與優衣庫相同),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重要性。毫無疑問的是,像別的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資品牌一樣,MUJI未合會重視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二三線城市(西南地域的成都聽說是今年多個品牌的“必爭之地”)。而走中低端道路的品牌較易在二三線城市擴展,價格優勢和品牌影響力將成為品牌的進入新市場的“敲門磚”。
對于那些想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分一杯羹的外資品牌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市場爭勝正在變得劇烈無比。因為國內外的價格差,那些有消費本領的顧客全部都跑去國外消費了,以至于不少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功勞出現下滑。
品牌商們已經感到到了事故的危急性。比MUJI行動快一點的是那個以雪地靴而有名的全稱美利堅合眾國品牌UGG。這家公司在上周也告訴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產品調價且已經在商店內實行新的價格,降價寬度大約在30%支配。“減少全球價格差距,爭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提供全球無不同的購物感想。”這家公司在郵件中如此回答記者。
品牌商們的價格鏖戰將要來臨。對于那些“買買買”的購物狂來說也許是個好音信。
“之前那些降價的傳言部分有誤。”無印良品(上海)商業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山本直幸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該品牌最終的降價時間是8月21日。
這亦是MUJI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后最大格局的一次降價。
并非首次降價
吳艷婷是MUJI的忠誠粉絲。早在2005年MUJI第一家專賣店進入的時候,她就開始購買這家的物品,現在她依舊會“沒事就去公司對面的店里晃一圈。”
“逛著逛著就會發覺有很多小驚喜。”她說,先前沒有想著要買的小雜貨,看到介紹和設計覺得精巧且實用,于是就會放進購物籃竹席里,“決定回家試試看好不好用咯。”
因為同是日本國品牌的聯系,MUJI常被外界用來與優衣庫做對照,但山本直幸卻并認為兩者相同,他認為反而和另一家瑞典公司宜家比較更加合適一些,“因為在MUJI所出售的物品里,差不多有一半是生存雜貨類用品。”
實際上也確實如此。MUJI的商業狀態清楚更加“復雜”一些。這家以生存方法為擴大方位的公司在內部把自己的在銷物品分為三大塊兒:衣著、生存雜貨(電竹席產品、家居用品、文具)以及食品類,離別占比約為50%、48%、2%。在食品類貨品沒有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時,前兩者則是各占一半,“所以,你很難說MUJI畢竟是一家賣衣服的公司還是賣生存用品的公司。”
有“死忠粉”的追捧,但價格一直是MUJI被“指責”的一點。
這個日本國品牌誕生于1973年原油危機時,那個時期日本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國家經濟增加明顯放緩。MUJI最初的定位就是去品牌化,追求沒有logo,生產簡易包裝甚至不包裝的生存物品,以提供較低廉的價格給大眾消費者。
脫胎于西友連環的“超級市場貨”,如今卻是國內各家大型購物中心開業時的熱捧的招商對象。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價格也自然是水長船高。
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賣出的物品標價上平常會有日本國的定價。經過匯價折算,消費者便可能知道同一貨品在國外的售價。“平常國內的價格要比日本國的貴一倍。”吳艷婷說,正是因為如此,在去年日元匯價大跌時,她“乘機”去日本國掃了不少貨,“那里的MUJI可低廉了呢。”
也許是感到到了這一點。MUJI從2014年開始調整其物品定價。
換而言之,此次的降價并不是MUJI在華的首次降價。山本直幸向記者泄露,從去年至今,該品牌已經調過三次價。第一次是在2014年的秋季,主要是一些衣著和生存類用品降價;第二次則是在今年的春季,只對部分衣著進行了調價,而第三次則是將要到來的這次。
雖然并不是早前傳言的全線降價,但加上之前兩次,被調價的產品數量的覆或然率并不低。
無印良品上海總部促販部的王黎雋說給記者,一個品類有能夠有四五個SKU(即保存庫存掌握的最小可用機構)甚至更加多,目前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SKU一共有5000個支配,如此算來,三次調價后,取得“新定價”的物品占比并不小。
據政府給出的數據,2014年秋冬的首次降價占全體物品的12%支配,2015年春夏的服裝雜貨類占到當時春夏全服裝類物品的37%支配,最新的這一次降價則占到全體物品的近50%。
調價背后的理論
對于記者提出為什么要調價的事故,山本直幸如是回答,“我們盼望店里的物品價格定價合適,足以讓喜歡的它顧客在出手(購買)時毫不猶豫。”他以MUJI的護膚品為例,我們的打扮品根本上都是日本國進口的,通過特惠規范,關稅減輕規程的申請,我們盡能夠的將因為進口部分的費用降低,從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價調整到顧客更易接受的水平。
在上海正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CEO崔洪波看來,MUJI的此次降價有兩方面要素。“首先,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銷量增加讓它具有降價的能夠。”據知道,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沒有自己的制成廠,產品均為OEM代工,“隨著該品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迅速開拓,生產要求也隨著賣出量加大,生產成本就可能降下來了。”
MUJ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時的生產成本降低這一點也得到了山本直幸的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市場要求越來越大,一次的訂購量增多,訂購生產成本單位價格自然就降下來了。”
記者知道到,在MUJI尚未完全擴張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門店不僅數量少,賣出額也很低,根源無法達到代工廠的最低訂貨量。同時,由于出關物品均被附上日語吊牌,第二次進關后的售賣產品還大概需要另加中文吊牌,僅此一項,生產成本不菲。
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門店和賣出額的增加,這一規模開始擴大變化。2010年起,MUJI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大格局“內販”,到2012年,服裝已全部實現“內販”,生存雜貨用品的“內販”率亦達30%。如此一來,物流和吊牌生產成本成倍下降。
此外,MUJI還通過減少不良率的方法降低代工生產成本。此前,由于品牌方對于產品要求較高,所以代工廠次品率居高不下。對此這些代工廠往往會事前要求增加超過10%的代工費用。對準這一難題,MUJI派駐一名日籍本質擔負,親自動手制作樣品,追溯整個生產工藝流程,并最終處理難題。經此,代工廠次品率、材料與人工生產成本均大幅降低。
崔洪波指出,近年來MUJI在華市場的迅速拓張也推動了這家公司選擇降價方式的另一個原由,“降低價格以轉移更多的消費者。”
記者得到,雖然MUJI在2005年就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其在國內市場真正開始“發力”則是在2010年后。2010年開始,這家公司開始以一年兩位數的開店數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大。2013年,MUJI“發作式”的開了37家店,算是得到了社長金井政明之前設定的“百店”打算。據山本直幸泄露,去年新增了30家,“今年的打算應該和去年差不多。”
從開店數量來看,除了日本國本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已經是MUJI全球的第二大市場(這一點與優衣庫相同),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重要性。毫無疑問的是,像別的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資品牌一樣,MUJI未合會重視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二三線城市(西南地域的成都聽說是今年多個品牌的“必爭之地”)。而走中低端道路的品牌較易在二三線城市擴展,價格優勢和品牌影響力將成為品牌的進入新市場的“敲門磚”。
對于那些想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分一杯羹的外資品牌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市場爭勝正在變得劇烈無比。因為國內外的價格差,那些有消費本領的顧客全部都跑去國外消費了,以至于不少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功勞出現下滑。
品牌商們已經感到到了事故的危急性。比MUJI行動快一點的是那個以雪地靴而有名的全稱美利堅合眾國品牌UGG。這家公司在上周也告訴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產品調價且已經在商店內實行新的價格,降價寬度大約在30%支配。“減少全球價格差距,爭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提供全球無不同的購物感想。”這家公司在郵件中如此回答記者。
品牌商們的價格鏖戰將要來臨。對于那些“買買買”的購物狂來說也許是個好音信。
- 上一篇:傳統紡織業觸網裂變 報喜鳥全面轉型為互聯網企業
- 下一篇:廠家工作服定做的流程